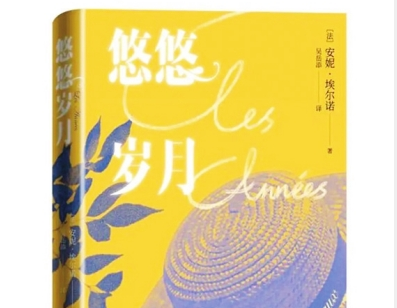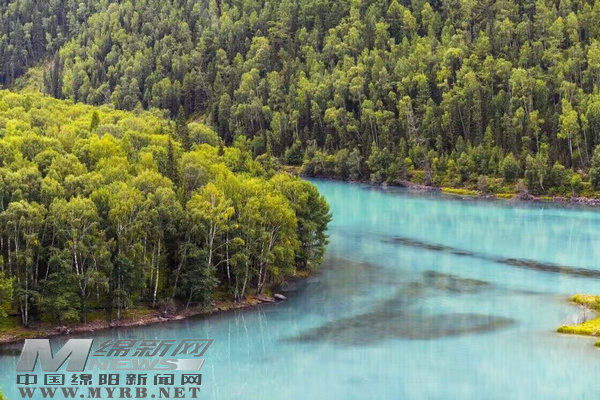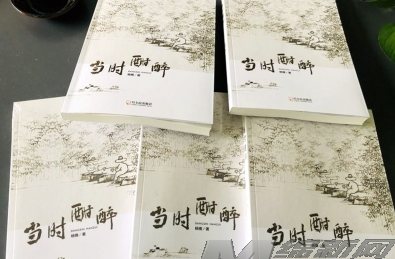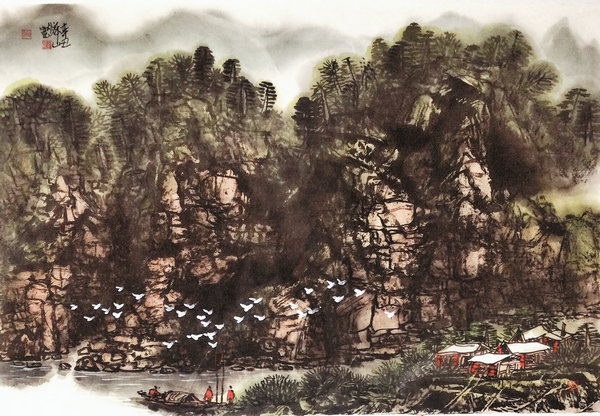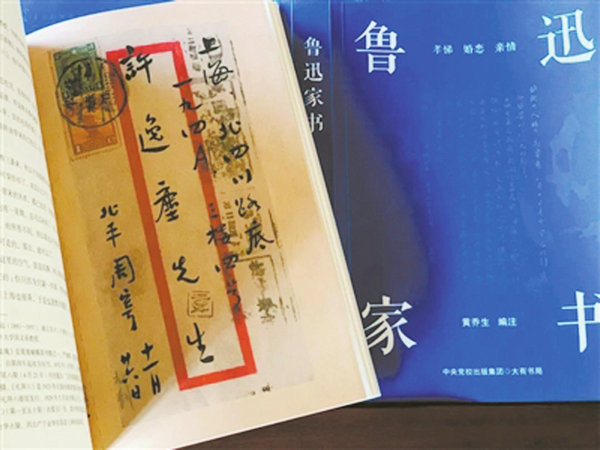□ 孟秀芳(上海)
上海大學圖書館擁有豐富的館藏資源,自1994年四校合并之后,圖書館擁有紙本文獻407萬余冊,電子書749萬余種。正如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說:“天堂就是圖書館的模樣”。是的,上海大學圖書館是書籍最高貴的棲身之所。
在這樣的環境中與書為伴,為我平生開啟了一種全新的認知。每天與圖書打交道,一本書從我手里至少經過幾遍,由陌生到熟悉,感覺過手的一本本書籍,如同一個個性格迥異的新朋友,它們各有各的外貌、特征與內容。每天與新面孔打交道,我的生活充滿了期待。能碰上讓自己眼前一亮的書確實不容易,《陽光中的過塵》就屬于讓我心動的一本書。這本詩集無論是內容安排還是裝幀設計,皆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似春的花開草綠,若夏的驕陽雨瀉,似秋的五彩與颯爽,若冬的凜冽與寂靜。
書的作者是四川詩人王開平先生,對我而言是一位素昧平生的牙醫,用詩人自己的話說:“一位對文字敏感而又敬畏的川北鄉巴佬”。在與他微信的閑聊中,得知這本詩集是他親自設計排版的,此書滲透了一位愛詩者的心血與智慧。一個背景、一句話,一張照片、一行詩,一種顏色、一幅插圖,那舒朗俊秀、詩配畫的頁面設計,不動聲色的文字表達……呼吸與脈搏,跳動與音符,在詩集中完美契合,這也許才是我真正喜歡的原因吧。
在詩人心中,也許牙齒和詩歌有著異曲同工之美吧!
不管詩歌的意象有多紛繁而隱匿,散文的內在有多絢麗而深邃,我想這一切的背后皆有定數。它們皆若陽光中的過塵,就像花開的聲音:“……/我很輕,一直輕到/塵世的內心,沒有一粒塵埃可依/我很輕,一直輕到/身體與血液中的岔路,情緒的對抗/被統統刪掉,就像/就像花開的聲音,輕輕看了我一眼”。
這也是詩集《陽光中的過塵》封面上的題句。
我非常喜歡這首詩。正如詩人王開平在該詩集的后記中所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大千世界、明媚陽光中的一粒塵埃、其間有歲月磨礪的痛楚,有成熟之后的平淡。在限定的歲月中,最終會化作灰燼消失在這萬丈紅塵之中,成為一粒過塵,這是人類無法躲避的劫數。”這一段文字是對該詩最好的釋義。
《陽光中的過塵》這本詩集,真真切切讓我怦然心動,而且愛不釋手。詩人只捐贈了一本給上海大學圖書館,詩集入館藏后我就沒有了。于是試著向詩人討要,詩人也不吝惜,不但送了我精裝本,還送了我8年前出版的詩集《寄回風中的牽掛》。
在詩集《陽光中的過塵》中,有很多首詩歌讓我潸然淚下。特別是詩歌《三寸天堂(組詩)》就是一個例證,它道出一個兒子在父親最后的時光里及父親離世以后,作為人子內心那種深入骨髓的疼痛與對親人遙遙無期的思念。那種失去親人之創痛酷烈,非一般人所能體會。
詩人王開平的詩歌《三寸天堂》,讓我再一次與詩人的情感共鳴。此刻我才真真正正感受到文學的力量。詩歌文本只是一種載體,每個人讀完之后所體現出來的那種意境可能沒有共性,但卻可以共情。這就是所有文學作品的共有特質與社會功能。
我與開平君是陌生的,對他的印象只停留在詩集《陽光中的過塵》精美的裝幀上,停留在每個頁面獨具匠心的設計上,停留在每一首詩歌傳遞給我的情景共鳴與觸動內心的靈魂對白的情感交融之中,如此一記。

編輯:郭成